
证券法下交易限制的法律规定及限制期确定:《证券法》的第36条明确规定了对依法发行的证券的限制期内股份转让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发行的证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特定股东在交易中需遵守这些交易限制。
此外,《证券法》第63条第2款也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在增减持过程中的报告和披露义务、限售义务做出了详细规定:“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5%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3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情形除外。”
另一方面,《证券法》第186条对限制期内转让股票的行政法律后果也有所规定:“违反本法第36条的规定,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或者转让股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限制交易的起算时点的确定:针对交易行为的违法定性为“限制期转让股票”,首要任务是明确限制期的起算时点。依据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适用理解,我们可以将《证券法》第63条第2款所规定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的披露及限售义务分为两种情形:
1. 情形一:当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数量”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例如,从11%降至9%),即便跨越了10%刻度,也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告。在公告后的3天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2. 情形二:即使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降至5%以下,即便“变动数量”未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例如,从5.5%降至4%),仍需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履行相关限售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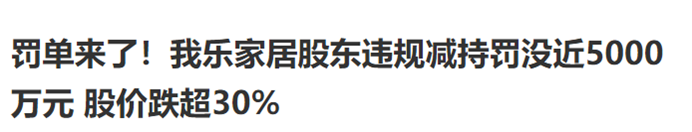
上述案例的独特之处在于,截至9月6日,投资者于某某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了”清仓式”减持WLJJ的行动(减持19,532,496股,占WLJJ总股本的6.1908%),同时触及了”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和”减持股份数量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这两种情形下的信息披露和限制交易义务。
对于确定本案限制交易期的起始时点,究竟应该以哪种情形为基础呢?
从监管部门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描述的违法事实来看,监管部门认定限制交易时点为情形一,即于某某及其一致行动人于9月6日9点51分49秒卖出WLJJ共计60,000股后,减持比例合计达到WLJJ总股本的5.0059%时,触及了限制交易时点。在情形一下,于某某及其一致行动人违规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为6,664,774股,占总股本的2.1124%。
然而,筆者认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认定值得商榷,本案适用情形二认定限制交易的起始点更为妥当。原因如下:
第一,《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已经对《证券法》第63条第2款的适用做了明确规定,即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降至5%以下时,应当履行披露及限售义务;反之,若不履行,则构成限制期交易。实际上,一旦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都会及时进行披露并停止交易。
第二,从违规增持的监管处罚案例来看,股东累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达到总股本的5%之后(如达到5.0062%)未披露亦未停止交易的,监管部门认定,自达到5%后至披露增持行为之日的交易行为属于违规增持。反之,减持过程中同样应当将持股比例下降至5%时作为限制期的起始点。
第三,若采用情形一对本案进行处罚,那么本案所涉及的交易行为的违法评价就显得不够完整。在情形一下,于某某及其一致行动人违规减持WLJJ合计6,664,774股,占总股本的2.1124%;而在情形二下,自于某某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最先降至5%的那笔交易开始(具体可根据集中竞价交易明细判断),其后的减持行为都应被视为限制期违规减持,情形二下违规减持的股份总量应当超过情形一的认定数量。
因此,无论是从现行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角度,还是从监管实践的角度来看,本案应以于某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的时点,而非合计减持比例达到5%的时点作为限制交易的起始点。
(二)关于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本案采用拟制成本法计算违法所得,涉及某某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违法所得总额约为1,653万元。鉴于数额庞大,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拟制成本法”的具体定义并未在证券和财会领域明确规定。字面上理解,拟制成本法指在无法准确计算真实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合理估算行为人的违法所得。然而,如何进行拟制仍未在现行法规文件中找到详细解释。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所列举的违法减持数量、金额、违法所得等数据,笔者计算出本案的拟制成本约为13.6元,略高于WLJJ在9月4日的收盘价。显然,该计算并非按照违法减持行为发生当日(9月6日)的股价,但具体的拟制成本计算方法依然缺乏明确说明。
(三)如何确定罚款数额
本案罚款高达3,295万元,罚款数额约等于违法所得的两倍,引发媒体普遍用“没一罚二”来形容本案的重罚。实际上,本案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券法》第186条与绝大多数法律责任条款不同——限制期减持的罚款金额不以违法所得为基数,而是允许监管部门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换言之,本案并非按照违法所得倍数罚款,而是在“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幅度内处以固定金额罚款,只是该罚款金额较为接近违法所得的两倍。
如何在“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范围内确定罚款金额?目前并无统一标准。《证券法》第186条规定了罚款金额的上限,但未规定下限。由于此类案件的交易金额往往巨大,涉及数额常达千万甚至上亿,罚款幅度的变化范围也相应较大。笔者对2022年限制期内买卖股票行为的罚款金额占买卖证券金额的比例进行统计,发现此类案例的罚款幅度差异很大,比例区间为2.09%到18.9%。
本案的罚款为3,295万元,占违法减持金额的30.7%,反映了监管部门对于违规减持行为采取重罚重处的执法态度。
在SXSW公司股份减持方面,股东朱某存在两项违规行为,分别违反了“在减持股份前,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予以公告”的承诺以及“减持价格低于公司发行价”的承诺。下面将对这两项违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
一、违反了“在减持股份前,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予以公告”的承诺
根据承诺,违反承诺收益的计算公式为:违反承诺收益所得=实际减持均价×(1−影响系数)×实际减持数量。而影响系数的计算采用了较为复杂的公式,即影响系数=减持计划披露后第4个交易日收盘价÷减持计划披露日收盘价。这一计算逻辑建立在假定股东在某一时间点事前发布拟减持股票的公告,考虑到减持预披露对“市场波动”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某一时间点”的选取日期不同,将导致影响系数结果的显著不同。
二、违反了“减持价格低于公司发行价”的承诺
朱某在2021年11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460万股,每股单价为45.97元,合计减持总金额21,146.20万元。根据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规定,朱某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不得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由于前述交易的成交价格低于公司发行价,朱某违反了招股说明书中有关减持说明的承诺。
根据公开信息,朱某的减持违规收益计算公式为:减持违规收益=(首发价格-实际减持价格)*减持数量。具体计算为(49.355-45.97)*4,600,000= 15,571,000元。
以上分析显示,朱某的减持行为不仅涉及了承诺违规,而且其减持违规收益巨额,值得公司和监管机构高度关注。
原文参见:invictus耀的法研库


